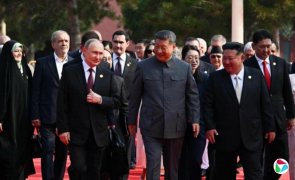美国联邦法院10月6日开启新司法年度。据媒体报道,多起涉及行政权边界、选举规则及公民权利的关键案件将陆续进入审理议程。这些案件涵盖关税权争议、独立机构负责人免职权、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成员任免权、属地主义原则下的出生公民权,以及跨性别者参与体育运动、州选区重划、枪支管制、竞选资金支出等10余项重大议题。与此同时,针对总统特朗普首任执政时期政策的系列诉讼,经相关上诉法院移送,亦进入联邦法院的紧急审理程序。
四大瞩目案件
据媒体报道,在该系列案件中,联邦法院就四项与特朗普总统政策密切相关的诉讼所作裁决备受关注:关税权争议、独立机构负责人免职权争议、特朗普试图解雇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成员丽莎·库克(Lisa Cook)案,以及出生公民权争议。这些案件直接关涉美国政体运行的权力边界,核心是对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持续扩张总统权力”行为的一次司法审查。
第一,关税权争议案。联邦法院将对特朗普政府实施大规模关税的合法性作出裁决。争议焦点在于总统能否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对多国商品征收互惠关税。上诉方主张,依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课征关税权属于国会专属权力,须经国会明确授权;特朗普政府则辩称,IEEPA赋予总统的管理进口权限已涵盖征收关税的权力。此案关乎总统行政权与国会立法权之边界。
第二,独立机构负责人免职权争议案。联邦法院将就总统对履行准司法和准立法职能的独立机构成员的免职权限,进行实体审理。此前,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劳特(Rebecca Slaughter)之举,实质上挑战汉弗莱遗产执行人诉美国案(Humphrey’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判例所确立的原则。该判例限制总统对此类机构官员的免职权。此案迫使联邦法院重新审视总统免职权的范围;特朗普政府主张总统拥有广泛的免职权,无须受限于“仅可因故解雇”的约束。
第三,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成员任免权案。此案关乎独立金融机构在美国政制中保持超然、中立角色的可持续性。特朗普试图解雇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成员丽莎·库克,直接挑战机构相对于行政权的传统独立性。法律依据是对《联邦储备法》中“因故”解雇条款的单方面扩大解释,并援引宪法赋予的行政权力。
第四,出生公民权争议案。此案核心在于质疑并试图推翻基于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属地管辖条款,对出生公民权的长期解释与实践。特朗普政府提出异议,主张第十四修正案中“受其管辖”者,不应包括无合法身份移民及临时签证持有者的子女,此举挑战1898年美国诉黄金德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所确立的判例。
上述案件的审理与最终判决,将进一步厘清行政权、立法授权与司法审查之间的界限,对重塑美国权力结构产生跨世代的深远影响,亦关乎即将届满20年任期首席大法官小约翰·格洛弗·罗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的历史定位。其中,关税权争议案的裁决,将于11月率先启动。
“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的滥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项案例共同揭示一个核心模式:特朗普试图通过主张一种超越常规的、宽泛的行政权力,挑战长期存在的法律先例、制度规范与权力分立格局。尽管并非每一项都严格依赖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紧急状态,但它们均共享一种在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至上的内在逻辑。
其一是关税权之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援引紧急状态的案例。特朗普政府试图将常规贸易争端,定性为国家紧急状态,激活《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总统的非常规权力。核心逻辑在于,因存在紧急状态,总统可以超越国会固有的关税立法权,实施单边行动,构成通过宣告“例外”创造权力的典型策略。
其二是独立机构免职权之争,该案例虽未宣告法律上的紧急状态,但特朗普所主张的“总统拥有广泛的免职权”本身,即构成旨在突破制度性制衡的“例外”主张。汉弗莱案判例旨在保障独立机构的准司法与立法职能,免受行政权不当干预,构成关键的制度性防火墙。特朗普则试图推翻该判例,实质是主张总统在人事任免领域,应拥有一种超越此制度框架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构成对权力分立常态的根本性挑战。
其三是美联储理事任免权之争,与前例类似,特朗普通过对《联邦储备法》“因故”解雇条款进行单边扩张解释,实质是在创设“例外”情形,以规避法律对美联储理事的明确保护。
其四是出生公民权之争,该案例是通过行政命令制造既成事实。特朗普借助签署行政命令,单方面重新解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试图颠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宪法实践。此举本质是行政权宣称,有权在常规的宪法修正程序或司法解释之外,直接定义公民身份这一根本性问题,也是一种“例外状态”的施用。
此系列行动的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行政权力的“例外”逻辑,冲击并重塑由国会立法、联邦法院先例及长期宪法实践共同构成的“法规范秩序”,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并扩张行政权力的外延。此现象实质上表征着美国政治文化,正经历急剧的退化与倒退。在法理层面,“例外状态”意指一种特殊的政治与法律情境,通常因严重危机(如战争、内乱、瘟疫、经济崩溃)而宣告。
宣告例外状态的行为本身,恰恰证明存在一种超越法律秩序的主权意志。依据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阐述,此种情境下的主权者,通过决断“例外状态何时存在”以及“如何应对例外”,将自身置于法律秩序之上。
此过程并非法律的适用,而是对法律效力的中止,直接动摇“法律为最高权威”这一根本前提。由此,主权者的决断取代普遍规则,行政指令取代法定程序。现代政治文明的演进,本是通过法律制度逐步驯化例外状态的过程,而特朗普的实践则开启此进程的逆转。
“保守主义革命”的悲歌
值得关注的是,例外状态或紧急状态的援引,或许并非被滥用,而是体现特朗普在实践一套完整的政治战争理论框架。依据卡尔·施米特的理论范式,战争作为最极端的例外状态形式,可能契合特朗普及支持者所推动的“保守主义革命”诉求,核心在于主张采取超法律的决断性行动,旨在颠覆现行政治体制,并将决断权直接指向所谓“深层国家”、主流媒体及“全球主义司法系统”。
在理论层面,例外状态恰恰构成“革命”的实践工具。就关税权而言,在自我界定的经济战争背景下,总统须被赋予类战时统帅的权威,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关税措施,抵御他国经济侵略。关于独立机构免职权,此类机构被视为深层国家的权力据点,充斥着意识形态对立者,要赢得文化内战,被认为须要具备“即时罢免”的权限,以实现对官僚体系的“革命性”改造。针对美联储独立性,被定性为服务于跨国资本而非本国公民的“全球主义金融系统”,主张通过专断性控制以重掌经济主权。至于出生公民权议题,则被建构为重塑美国人口结构与文化认同的生存性斗争,关乎国家政治文化的根本走向。
值得反思的是,特朗普着力推进的保守主义革命,以专断权力与例外状态全面推行保守主义议程的路径,实质上侵蚀保守主义自身的文化根基。
为实现保守主义的政策目标,他采用方法论上完全背离保守主义原则的手段,在根本上瓦解保守主义赖以存续的文化与制度基础。古典保守主义的内核在于审慎精神、传统价值,以及对权力尤其是不受约束的集中化权力之深刻警惕——这种警惕基于人性认知,无论掌权者身份为何。特朗普最大限度地扩张行政权力,持续以例外状态挑战法治秩序,本质上正构成对保守主义核心价值“有序自由”的根本性解构。
媒体曾指出,自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联邦法院中保守派多数法官屡次通过影子诉讼程序(即发布简短命令、不附详细裁决理由书),对特朗普政府予以隐晦支持。然而,本次系列案件触及美国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的根本界限,在某种意义上关乎美国政体前景。不知届时的保守派大法官,是执着于保守派的权力,又或是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审慎、传统与对权力的不信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