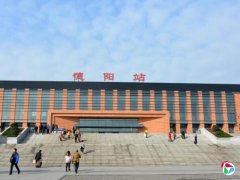密密麻麻的展板前,年轻人一批批围上来。有的在纸条间扫视,有的停下脚步,还有人挤过人群,把新的纸条贴上去。
深秋的午后,上海年轻人聚在鲁迅公园,参加一场户外“文学节”。主办方准备了纸和笔,谁都可以当场提笔,写下对生活的感悟。
在周末活动让人挑花眼的魔都,本以为这样的文学活动是小众的。但到了现场,看到入口处长长的队伍,我还是愣了一下,这届年轻人重新拾起文学了?
在现场的图书市集和互动装置转了一圈,我很快找到了答案。与其他的文学节不同,这里的主角不是名师大家,而是普通人身边的“素人写作者”。

70岁的广西老妪“肖大妹”,磨了半世豆腐,五年前开始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画出来,这次在现场办起自己的“人生画展”。同样70岁的河北退休教师王玉珍,一年多前写下已故丈夫的故事受到关注,今年带着刚出版的第一本书,在现场签售。
潮汕年轻人阿林做纸钱批发生意,他关于文学的比喻被制成文字装置,吸引不少人拍照打卡:“生活和文学的关系,就像是公路和绿化带。没有绿化带,公路也能照样运转。但有了绿化带,你可以看到光的轮廓、树的影子、风的形状,这个世界也会可爱一点点。”
中国接入互联网以来,2000年后曾经历过一轮网文小说和草根文学的兴起。当时的代表作者如打工妹诗人郑小琼,写下“十四岁小女孩要跟我们,在流水线上领引时代带来的疲惫”,让人们窥见广东流水线女工的真实生活;也有“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把岩层一次次炸裂”的矿工诗人陈年喜,让人随他的文字走进矿山。
过去几年,书写普通劳动者生活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2023年,外卖诗人王计兵两本诗作《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先后问世;同年,打过19份工的胡安焉出版了《我在北京送快递》,被评为当年豆瓣“年度图书”,迄今已售出200万册。
去年,从河南来到上海做司机的黑桃,将出租车里的故事写进《我在上海开出租》;今年9月,“90后”外卖女骑手王晚也出版了自己的首部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豆瓣评分高达8.6分。
为什么各类打工文学不断涌现?《经济学人》在《我在北京送外卖》英文版的书评中,将这部作品引发共鸣归结为经济因素:在企业大规模裁员、降薪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劳动者被推向零工经济。读到胡安焉经历的那些挫折,他们多少能从中获得安慰,因为他们自己也在摸索着应对一个变化、放缓的经济。
截至去年底,中国零工就业人数已超过2.4亿人,如此庞大的群体,的确构成这类作品的读者基础。但仅用经济解释来概括这波写作潮,显然仍不够。
也有评论认为,底层写作密集出现,是“一场制造中的文学现象”。社交媒体的流行,加上非虚构写作的热潮,为普通人的表达提供前所未有的传播条件,让这些声音集中“冒”了出来。
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社媒降低了写作门槛,也让“素人文学”能够迅速扩散。然而,在短视频和短剧占据注意力的时代,再有张力的文字、再厉害的算法,恐怕也不足以将文学重新送到前台。必然有某种东西,是文学所独有、也无法替代的。
在文学节期间一场论坛上,陈年喜谈到文学的意义时说,教科书把文学拔得太高,其实文学的基本功能,是让不同群体、不同命运彼此看见。“我们都处在一个非常孤立、黑暗的世界中……写作的意义,是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世界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这样生活,他们有这样的喜怒哀乐。”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行业震荡频繁,普通人的生活节奏被反复打乱。许多人成为系统中的指标、公司里的成本,或是城市里一份可被替换的劳务合同。在这种抽象化的日常里,阅读一个具体的人、一段具体的命运,成了一种“把自己找回来”的方式。
回到当下的中国年轻一代。他们成长于物质丰盈的年代,既对外部世界怀有好奇,也更愿意向内探索生活的意义。他们愿意倾听,也愿意用文字表达感受。这也许是为什么,社媒平台小红书的这场“身边的写作大赛”今年办到第二届,投稿量翻了一倍多,达到近4000万字。
这也说明,文学并没有消失。相反,我们或许比过去更需要它。当我在活动现场,看到阳光照在印着一句话的墙上,年轻人排队与它合影时,这种感觉愈发清晰。墙上写着:“所有与文学失散的人,总有春天再相逢。”